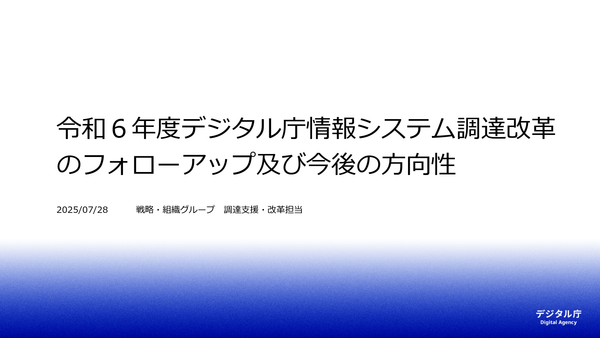蘇哈托政權垮台後印尼的反華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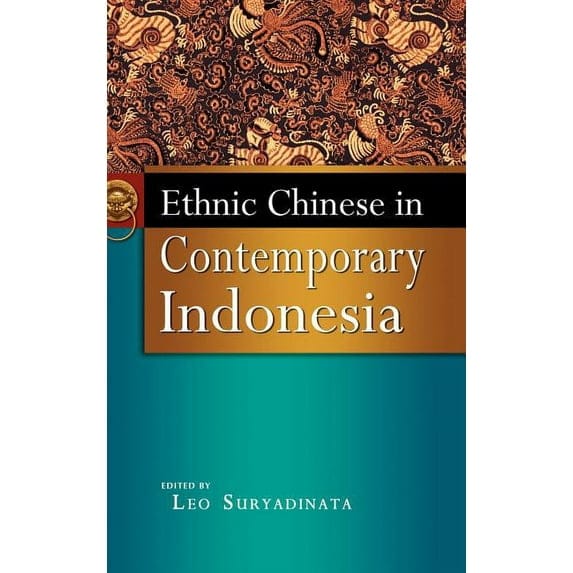
原章節名稱: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AFTER SOEHARTO
作者:Charles A. Coppel
「反華暴力」這個概念已經成為印尼相關寫作中的陳腔濫調。任何關於反華暴力爆發的新聞報導都可能包含以下要素:對印尼華人數量的粗略估計;聲稱他們在財富上不成比例地富有;提及反華偏見和歧視(特別是在蘇哈托政權下);以及斷言反華暴力在印尼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以這種方式陳述,這些命題似乎無可厚非。但這些要素經常被扭曲和誇大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影響了對所討論暴力事件的報導和理解。
早期反華暴力的扭曲與誇大
反華偏見和歧視在印尼確實存在,並且長期以來一直是反華暴力爆發的根本原因,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這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已經被扭曲成接近大屠殺規模的幻想。例如,維基百科上「印尼華人」條目(截至2007年6月22日)提到1965年「數百萬印尼華人的屠殺」以及「兩次種族滅絕暴動……在1965年和1998年」(Wikipedia 2007)。這種荒謬的說法呼應了傑克·皮澤(Jack Pizzey)1988年電影《泗水慢船》中的無稽之談,他在片中說1965年「成千上萬的[華人],也許是數百萬人,被印尼人屠殺」(Pizzey 1988)。
將1965-66年印尼大屠殺描繪為反華種族滅絕的做法甚至影響了所謂的學術寫作。根據少數族群權利組織2000年發表的東南亞華人報告:
「被殺害的華人確切數字仍然不明,但這個數字可能達到數十萬人(Chin 2000, p. 14)。」
作者在尾注中補充道:
「一些評論者認為華人傷亡人數是數萬而非數十萬(Chin 2000, p. 33, endnote 10)。」
但他沒有為這兩個估計提供任何來源,甚至沒有暗示數十萬非華裔印尼人也遭到屠殺。
瑪麗·海德赫斯(Mary Heidhues)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由林潘編輯)中關於「印尼」的條目呈現了更加冷靜和準確的圖像(Heidhues 1999, p. 166):
這種騷擾使一些評論者將成千上萬人的暴力和殺戮視為反華大屠殺。雖然確實有數千名華人喪生,但被殺害的人數比例上少於印尼原住民。1965-67年的暴力是針對共產黨人或疑似共產黨人的,而不是針對華裔的。
這個判斷與我自己的研究以及羅伯特·克里布(Robert Cribb)的研究一致,後者是1965年印尼殺戮事件的權威專家。1965年印尼大屠殺中被殺害者的確切人數永遠不會為人所知。但受害者絕大多數是爪哇人和峇里人,而不是華人;這場屠殺是政治滅絕而非種族滅絕(Coppel 1983, pp. 58–61; Cribb 1990)。
在1998年五月暴動案例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扭曲和誇大。將其——以及1965年的暴力——描述為「種族滅絕性的」,正如前面提到的維基百科條目所做的,是在貶低「種族滅絕」一詞的含義。在這兩個案例中,被殺害者的確切人數都缺乏確定性,但在1998年的案例中,在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內有幾次建立事實的嘗試,儘管相互矛盾(Purdey 2002)。這些嘗試都不支持殺戮在規模或受害者構成上具有種族滅絕性質的觀點。聯合真相調查小組(TGPF)在1998年10月23日關於1998年5月13-15日暴動的最終報告中,列出了各種來源確認的雅加達地區死亡人數:1,190人(人道主義志願團隊[TRuK])、451人(警方)、463人(雅加達軍區司令部)或288人(雅加達政府)(TGPF 2001, p. 345)。大多數受害者在雅加達購物中心被燒死。這些購物中心為華裔所有,但受害者絕大多數是非華裔搶劫者,據人道主義志願團隊的一名成員說,他們「來自小公務員、臨時工、洗衣工和家庭傭人的家庭」(Farid 2006, p. 273)。
反證
那些宣揚對印尼華裔如此根深蒂固和普遍敵意的人,將如何解釋以下五個近期現象?
• 中國新年現在是印尼的國定節日和假期。2007年,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總統出席了在雅加達展覽場舉行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該活動在國家電視台進行了現場直播。
• 自2004年10月以來,華裔印尼人瑪麗·潘格斯圖博士一直擔任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總統治下的印尼貿易部長。郭建義曾在梅加瓦蒂·蘇卡諾普特麗總統治下擔任國家規劃委員會國務部長/主席(2001年7月至2004年10月),並在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總統治下擔任經濟、財政和工業統籌部長(1999年10月至2000年8月)。
• 2006年8月1日,新的印尼公民身份法(法律第12/2006號)生效,其中「印尼原住民」(orang-orang bangsa Indonesia asli)一詞被重新定義為那些在出生時成為印尼公民且未自願接受任何其他公民身份的人。這一變化消除了歧視印尼華人的主要法律依據。
• 2007年4月3日,印尼國防部秘書長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北京簽署了一項國防和安全事務諒解備忘錄。幾週後,中國駐印尼大使蘭立俊表示,「自2005年以來,兩國已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和軍事領域」,中國政府歡迎印尼提出的任何不附帶政治條件的購買中國軍事裝備的建議(雅加達郵報網站2007年4月20日,BBC全球監測服務報導;另見雅加達郵報2007b)。
• 中國和印尼最近同意加強文化聯繫,以增加兩國之間的旅遊業。印尼文化和旅遊部長傑羅·瓦奇克表示,印尼希望在2007年接待至少30萬中國遊客,而2006年為8萬人。2006年到中國的印尼遊客有20萬人。傑羅宣布兩國計劃聯合製作一部關於鄭和遠征的電影,「以說明印尼和中國之間數百年來的文化聯繫」。《雅加達郵報》的一份報告說,來自中國的文化對印尼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雅加達郵報2007a;Taufiqurrahman 2007)。
如果非華裔和印尼華人之間的敵意如有時所暗示的那樣根深蒂固和激烈,人們可能會期待對這些發展產生劇烈反彈。我在這方面可能消息不靈通,但據我所知,它們還沒有(或尚未)引起任何波瀾。我並不打算走向另一個極端,暗示中國和印尼之間的關係(或印尼華裔和非華裔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沒有摩擦。即使現今的部長級公關人員希望如此,那也是荒謬的。這裡的問題是平衡、認真公正的表述。
我也不是在暗示1965年或1998年沒有發生反華暴力。當然發生了。但是,重申一下,在這兩個案例中,因暴力而死亡的絕大多數人是原住民(pribumi)印尼人,而不是華人。暗示其他情況是誤導性的,如果不是惡意的話。正如我在《危機中的印尼華人》中所寫:
總的來說......在政變後初期,反華暴力最典型的形式不是殺戮、人身暴力或監禁,而是財產損害,如搶劫、掠奪和燒毀商店、學校、房屋和汽車(Coppel 1983, p. 58)。
比較1965年和1998年
三十年後,從1996年中期開始並在1998年5月達到高潮,又發生了廣泛而大規模的反華暴力,同樣主要表現為財產破壞。然而,存在一些重要差異。
最重要的差異之一是媒體和學術寫作對反華暴力報導程度的不同。1965年當時媒體幾乎沒有此類報導,學術寫作也很少(Coppel 1983; Mackie 1976, 1980)。相比之下,1998年的反華暴力受到了媒體的飽和報導(特別是透過網際網路的電子媒體)和相當多的學術關注。關於英文文獻的樣本,參見Ang 2002; Coppel 2001; Heryanto 1999; Kusno 2003; Leksono 2001; Lochore 2000; Purdey 2002, 2005, 2006a and b; Sai 2006; Sidel 2001, 2007; Siegel 1998; Tan 2006; Tay 2000, 2006; 以及Wibowo 2001。我認為,令人驚訝的不是1998年暴力的報導程度。這場暴力發生在包括首都雅加達在內的主要城市中心,在全世界電子媒體的注視下。這是數月緊張局勢升級的高潮,並導致了掌權三十多年的蘇哈托總統辭職。需要解釋的是1965年暴力總體報導相對較少,以及許多人(特別是媒體)傾向於將華人視為受害者的趨勢。第一個問題在西方媒體表述中可能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冷戰環境,以及自由民主國家不願承認大屠殺可能是由有政治動機的反共產主義者故意為之。將如此大規模的暴力以種族或原始術語(印尼原住民和華裔之間數世紀的仇恨)解釋,或歸因於所謂印尼人/馬來人天生的暴力傾向(並指出這個英文詞彙的起源是馬來語/印尼語詞彙amok或amuk),是更容易的做法。
1965年暴力和後來的暴力之間,第二個主要差異是1998年對婦女的可怕輪暴。這個因素是世界各地表達憤怒的主要原因,特別是在海外華人中。與被殺害的人不同,強暴受害者確實主要是華裔婦女。1998年輪暴事件報導中最具煽動性的面向之一,是在網站上張貼被殘酷折磨婦女屍體的照片(並作為電子郵件附件傳播)。這些屍體被確認為在五月暴力中被強暴的華裔婦女,並作為這樣的照片在媒體上轉載。事實上,其中一些照片是在東帝汶被印尼軍方和民兵成員蹂躪的非華裔婦女。這些照片早在1998年5月之前就已經在東帝汶國際支援中心(ETISC)網站上公開展示。當披露這些照片是「假的」(換句話說,它們根本不是華裔婦女屍體的照片)時,那些否認1998年5月華裔婦女強暴事件曾經發生的人將此作為彈藥,對抗那些試圖確立這些事件為事實的人(Sai 2006; Tay 2006)。隨後在印尼內外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議。
分析與表述框架的重要性
這再次說明了將針對華裔的暴力與其他暴力爆發孤立看待的廣泛且扭曲的傾向。那些可能為東帝汶婦女辯護的人在哪裡?這些婦女的屍體如此公開地在這些圖像中展示,她們是這種殘酷性暴力的受害者。針對華裔婦女性暴力的論述,忽視了印尼其他婦女遭受的類似暴力,這等同於特殊辯護。在印尼以外並不廣為人知的是,1998年5月強暴事件,是哈比比總統成立全國婦女暴力委員會(Komnas Perempuan)的觸發因素,該委員會將群島其他地方針對婦女的性暴力列入議程,包括亞齊和東帝汶(Tan 2006)。
我的觀點是,對暴力的詮釋關鍵,取決於其表述的框架。如果框架是原住民對華人的古老仇恨,就會導向特定類型的結論;如果框架是軍方和民兵對平民的殘暴,則會帶你走向另一個方向。這實際上是一個更大問題的一部分。在有華裔受害者的暴力案件中,什麼情況下我們有理由稱這種暴力為「反華」暴力?如果原住民員工因工作條件受剝削而毆打他們的華裔雇主,這是「反華」暴力還是基於階級的暴力?如果原住民穆斯林燒毀一座基督教教堂,而會眾中包括一些或許多華裔基督徒,我們應該將此視為「反華」暴力還是針對基督徒的暴力?我認為這些問題沒有先驗的答案。它們也不一定是我在這裡提出的非此即彼的問題。在同一個案例中可能混合了階級、種族和宗教因素,事件可能被他人出於政治目的挑撥或操縱。每個案例都需要根據現有證據進行檢視。正如麥基(Mackie)(1976, pp. 129–37)指出的,造成群體對立傾向的因素、抑制敵意表達的因素,以及在緊張局勢中引發暴力的因素,都是多重且複雜的。
要知道特定因素有多表面或多根深蒂固也可能非常困難。例如,麥基引發因素中的第六項涉及「公開表達或炫耀文化和種族差異」,如舞獅(barongsai)遊行,他說這是「挑撥性的」,是「在印尼土地上對中國性的公開示威或宣示」(他的強調),是「對印尼民族主義的冒犯」,至少在「極度緊張時期」可能引發反華暴力(136)。在蘇哈托時代,中華文化的公開表達被官方禁止,印尼華人被告知「慶祝中國新年(農曆新年)的活動應該在家庭內部或個人進行」(Coppel 2002, pp. 213–26)。自1998年以來,這項禁令已被推翻,程度之大以至於中國新年現在如上所述成為印尼國定假日,其慶祝活動在國家電視台現場直播,甚至印尼主流政黨也在選舉活動中使用中國舞獅(barongsai)。現在甚至有全國舞獅節(雅加達郵報,2007c)。當然,在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總統的繼任者治下情況可能會改變;人們很容易想像目前在哪些情況下表演舞獅可能產生挑撥性、觸發性效果(例如,如果在齋戒月期間未經事先同意在清真寺前表演)。背景至關重要。
麥基的另一個引發因素是與中國的關係狀態(135),特別是如他所說,「如果北京的反應是印尼人認為具有挑撥性、威脅性或干涉性的」,如1959-60年和1965-67年。另一方面,他寫道,「兩國政府關係變得更密切這一事實,是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在1963年5月],儘管北京沒有說或做任何讓蘇卡諾政府難堪的事情」,因為「萬隆和其他地方一些反華暴動煽動者的動機之一似乎是要破壞與中國的關係……」如果我們看看今天的情況,世界國際秩序中的主要斷層線不再是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陣營之間的斷層線,在那裡反共的印尼軍方可能將印尼的華裔視為共產主義中國的潛在第五縱隊。主要的國際斷層線現在更多地位於中東和「反恐戰爭」。中國已放棄干預印尼內政,在印尼也不被視為伊斯蘭教的威脅。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新的雅加達-北京軸心(poros)可能正在形成,軍事和文化協議正在進行中,中國經濟巨輪可能像在澳洲一樣被視為國內經濟增長的動力。
蘇哈托政權垮台後的反華暴力
在完成這些開場白和注意事項後,我終於來到了蘇哈托垮台後印尼反華暴力的問題。什麼反華暴力?約翰·西德爾(John Sidel)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暴動、大屠殺、聖戰》(2007)中斷言,1998年後,「熟悉的反華暴動和教堂焚燒劇目從印尼公共生活的舞台上消失了」,除了在雅加達權力轉移後幾個月內在普爾沃勒霍(Purworejo)和卡拉旺(Karawang)發生的少數「所謂的反華暴動」(Sidel 2007, p. 2, 135;另見Sidel 2001, p. 59)。他認為這是「值得檢視的重要變化」,並寫道:
與根深蒂固的「種族仇恨」或「經濟怨恨」的假設相反,全國普通印尼人面臨的失業、通脹和困苦的浪潮上升,以及對民眾動員威權限制的放鬆,在1998-99年並沒有結合起來導致反華暴動的回歸,更不用說此類騷亂頻率或暴力程度的升級(Sidel 2007, p. 136)。
為什麼沒有?西德爾的解釋嵌入在一個關於印尼宗教暴力形式轉變的複雜論證中,從暴動(1995-98)到大屠殺(1999-2001)再到聖戰(2000-04)。我不打算在這裡詳述該論證,只是想提請注意他對第一階段(「暴動」)的說法,當時發生了他所謂的「所謂反華騷亂」,其中「群眾攻擊、破壞和焚燒印尼華人擁有的商店、超市、百貨公司、商品和其他財產;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及其他宗教場所;以及警察局和其他政府建築物」(Sidel 2007, p. 1)。西德爾在這種情況下反覆使用「所謂」一詞,以及在談到1998年5月後的普爾沃勒霍和卡拉旺暴動時,暗示當華裔是受害者時,他可能不願承認種族或種族因素的作用。
傑瑪·珀迪(Jemma Purdey)沒有這種勉強。在她最近出版的著作《印尼反華暴力,1996-1999》(2006)中,她觀察到「他們的種族身份意味著印尼華人總是脆弱的」(Purdey 2006a, p. 30)。對她來說,儘管如西德爾所暗示的「『反華暴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從政府和公眾言論中消失了」,但「針對華人的暴力事件並未停止」。根據她的說法,「全國言論可能已經改變,但地方現實沒有改變」(Purdey 2006a, p. 211)。
我們再次發現背景可以影響分析。這是兩本優秀而複雜的書,但它們不同的框架(西德爾的宗教暴力,珀迪的反華暴力)導致了不同的結論。儘管存在這些差異,它們似乎在根本上同意:自蘇哈托以來反華暴力已經減少。西德爾可能誇大了1998年5月後過渡期間下降的程度,實際上珀迪確實確定了該期間除他提到的普爾沃勒霍和卡拉旺之外的其他一些案例(Purdey 2006a, pp. 219–20)。然而,我認為無可爭議的是,此後印尼反華暴力的發生率非常輕微。事實上,我在過去七年中只遇到了兩起報告案例(我將在下面討論)。正如西德爾所說,這種下降是值得檢視的重要變化,特別是因為在此期間還發生了其他重大和持續的暴力爆發。這些暴力從安汶(馬魯古)、桑皮特(中卡里曼丹)和波索(中蘇拉威西)的群體暴力,到峇里島和雅加達的聖戰炸彈襲擊,再到針對東帝汶、亞齊和巴布亞被指稱分離主義者的國家資助暴力。
我上面提到的反華暴力的特殊案例發生在雅加達(2000年)和錫江(2006年)。兩者都發生在1998年5月暴力週年紀念日或附近。2000年5月事件發生在雅加達唐人街格洛多克(Glodok)地區。暴動者向店面投擲石塊,在街道中央焚燒桌子,與警方發生衝突,警方發射催淚彈並與暴動者進行近身戰鬥。一家BMW展示廳、一家麥當勞餐廳和電子商店遭到嚴重破壞。警方發言人說,超過一百人被審問,十一人因煽動暴動者而被逮捕。二十名警察受傷,暴民逃離後數百名警察在街上列隊。這起事件不僅在規模上比兩年前發生的事件要小得多,其動態也大不相同,華裔並不是暴力的目標。暴動是由警方黎明前突擊搜查非法影音光碟銷售商引發的。憤怒的小販和失業群眾對突擊搜查做出暴力反應。警方顯然盡力保護華人免受暴力侵害。這個敘述中未解釋的是,為什麼安全部隊選擇在1998年5月事件二週年當天進行突擊搜查(Firdaus 2000; Go 2000)。
據媒體報導,錫江的一名印尼華人男子據稱折磨兩名原住民女傭,其中一人後來死亡,在2006年5月10日引發了「無政府主義學生抗議」。抗議活動次日繼續,但參與的學生與早先的「無政府主義行動」保持距離。報紙報導對實際發生的事情描述含蓄,但許多華人擁有的商店都關閉了(Editorial 2006; Hajramurni 2006a and b)。這個案例是許多印尼華人已經視為「正常」的暴力類型的典型例子,即印尼華人作為一個群體要為個人的被指稱罪行負責,「無政府主義」抗議者以破壞他們的財產形式進行粗暴的即決審判。這種行為的原因——可能被像交通事故這樣相對微不足道的事情觸發——對生活在法治社會中的人來說並不立即明顯。《雅加達郵報》社論認為:
錫江的暴動可以被視為對許多人面臨的當前經濟困難的憤怒和沮喪的表達。被折磨的女傭是弱者的象徵,而嫌疑人是那些利用權力踐踏不幸者的象徵。
一名學生活動人士據報聲稱,抗議是「一種自發的團結行為,旨在敦促警方徹底調查案件,而不是與嫌疑人『私下交易』」。哈薩努丁大學社會學家 Muhammad Darwis 表示:
不公平的待遇成為當地人對印尼華人不滿的根源,後者慢慢控制了經濟部門。這種感覺就像一顆定時炸彈隨時準備爆炸......特別是因為地方政府現在也傾向於為印尼華人商人敞開大門。
據說進行了華人和錫江布吉人(Bugis)社會互動研究的 Darwis,將印尼華人的「排他性」歸咎於他們與當地人缺乏互動,他說當地人是「一個能夠容忍差異的開放社區」。他補充說,「也存在社會嫉妒,因為人數不多的印尼華人控制著經濟並受到政府的青睞」(Hajramurni 2006b)。
記憶、歷史與正義 vs 失憶、沉默與逍遙法外
每年五月,人們聚集在一起紀念1998年的暴力事件。他們舉行守夜、集會和遊行,拜訪因暴力而死亡的親人墳墓,並呼籲政府查明誰策劃了暴力事件並將其起訴。2007年的紀念活動以努山達拉團結組織(SNB——祖國團結)和印尼律師和人權捍衛者協會(APHI——印尼律師和人權捍衛者協會)出版的一本書的發佈為特色。該書長達470頁,配有彩色照片,標題為《1998年五月暴動:事實、數據與分析》。四人團隊的主要作者是埃斯特·英達亞尼·尤蘇夫(Ester Indahyani Jusuf),她是一名律師,也是SNB不懈的主席和推動力。作者們打算讓這本書超越呈現事實、數據和分析,這可以從其副標題《揭露1998年五月暴動作為反人類罪行》中看出,但他們解釋說,由於擔憂,這並不可行,並承諾SNB將單獨發表完整的法律分析。
在2007年5月13日發表於全國性日報《羅盤報》的一篇文章中,阿里爾·赫里揚託(Ariel Heryanto)指出,九年前雅加達的暴力持續了幾天而當局沒有任何阻撓,但從未有一個人因參與該事件而被調查,更別說起訴了。他對他認為廣泛存在的誤解感到遺憾,即所發生的是「原住民」多數對華人少數群體發洩的種族暴力。儘管他並不否認存在種族因素,考慮到華裔受害者的突出性,他更願意關注他所看到的社會中無意識的厭女性別歧視,特別是在主要是男性的領導者中。這是一種需要解決的社會病症,將1998年五月強姦視為種族暴力使大部分公眾能夠將其視為不影響他們的事情。
未能將那些對1998年五月暴力負責的人繩之以法,不幸的是在印尼並非孤立現象(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01)。即使在1965年後近半個世紀過去了,二十世紀最嚴重屠殺之一的責任人沒有一個被追究責任。那些被認為犯有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印尼人不僅大多數沒有被起訴,而且還曾經並繼續擔任高職。正如《雅加達郵報》2007年5月18日的一篇文章(「1998年五月暴動仍然只是另一個致命謎團」)指出的,在1998年暴動期間在雅加達擔任重要職務的高級軍警官員都未受到觸動,包括雅加達軍區司令少將沙弗里·沙姆蘇丁(Sjafrie Sjamsoeddin)、雅加達省長少將蘇蒂約索(Sutiyoso)和雅加達軍區參謀長准將蘇迪·西拉拉希(Sudi Silalahi)。沙弗里·沙姆蘇丁(現為中將)是印尼國防部秘書長,於2007年4月在北京簽署了國防和安全事務諒解備忘錄;蘇蒂約索(現為退役中將)仍然是雅加達省長;蘇迪·西拉拉希(現為退役中將)是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總統的內閣秘書。
可以理解的是,當這些和其他關鍵軍政人物繼續擔任如此具有影響力的職位時,1998年強姦受害者保持沉默。她們知道出現任何新的政府對1998年五月暴力調查的可能性極小,並且非常清楚公開發聲的風險。瑪塔迪納塔(Marthadinata)的被殺——她是人道主義志願團隊(TRuK)的一名十八歲成員,在她準備於1998年10月離開美國就強姦案作證之前被殺——足以威嚇TRuK成員,並且一定增加了強姦受害者在公眾面前作證的自然勉強(Purdey 2006a, p. 146)。
雅加達和其他城市的1998年五月暴力對印尼華人來說是一個轉折點。伊格納修斯·維博沃(Ignatius Wibowo)(2001)論證說,它「促使他們行動」,他識別出三種回應類型:「退出」、「發聲」和「忠誠」。通過採取「退出」選項,他們可以逃往國外或印尼某個更安全的地方,或選擇「內部退出」,即留下來並在房屋周圍建造更高的鋼柵欄。通過採用「發聲」策略,他們可以為消除歧視性立法和做法而運動,並鼓動起訴暴力肇事者。他說絕大多數人選擇了剩餘類別「忠誠」:
他們照常生活,試圖從現有情況中獲得最佳結果。他們沒有抗議不公正的情況,但希望並相信事情會改善(Wibowo 2001, p. 143)。
這段引文暗示的是被動而非行動,但他在「忠誠」類別中包括了那些組建或參與政黨的人。
那些追求「發聲」策略的人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大部分歧視性立法已被移除,公開示威或中國性的宣示似乎不再被視為挑撥性的。關於變化程度的進展報告可以在《亞洲族群》期刊2003年10月特刊(「發聲:蘇哈托後的印尼華人」)中找到。然而,那些試圖將暴力肇事者繩之以法的人沒有取得這樣的成功。儘管國家人權委員會(Komnas HAM)在2003年重新開始對1998年五月暴力的調查,但建立特別法庭聽取證人證詞的嘗試無果而終(Purdey 2006a, p. 217)。
珀迪認為,「缺乏對1998年五月暴力受害者的任何制度性正義和癒合過程阻礙了新民主印尼『華人問題』的解決」。正如她指出的,這樣一個「肇事者對其行為表示悔恨,國家讓他們對反人類罪行負責」的過程
對新秩序的所有受害者同樣重要,包括1998年和1999年在Semanggi被殺的學生、1998年五月的印尼華人受害者、1984年丹戎不祿的穆斯林受害者以及1999年遭受痛苦的東帝汶人。未能提供正義機會和公開紀念這些事件,等同於說這些受害者的痛苦並不重要(Purdey 2006a, pp. 216–17)。
我想在這個名單中加上1965年和1966年暴力的數十萬受害者。
在這一點上,我們被迫面對印尼暴力受害者正義和癒合面臨的任務規模。規模是巨大的,與後種族隔離的南非不同,舊政權並未完全被推翻。正如 Mary Zurbuchen 就1965年暴力所寫的:
很誘人地希望通過系統性檢查......印尼可以產生一個和解與衝突解決過程,這將減輕目前正在目睹的持續暴力和新群體主義。然而,現實中,正式的尋求真相過程可能不會導致社會癒合......在後蘇哈托關於人權的法律和立法激增、官方調查以及關於腐敗和司法的國家委員會中,對協調嘗試重新審視過去的倡導必須與印尼改革議程中的許多其他優先事項競爭(Zurbuchen 2002, p. 581)。
我分享她的悲觀主義,也分享她對保存普通印尼人證詞需求的認識,「如果關於印尼1965年大屠殺和持續的群體和政治暴力模式以及如何防止其再次發生的更大問題,要得到回答的話」(Zurbuchen 2002, p. 581)。阿斯維·瓦曼·亞當(Asvi Warman Adam)、布迪阿萬(Budiawan)、希爾馬·法里德(Hilmar Farid)、埃斯特·尤蘇夫(Ester Jusuf)、凱特·麥格雷戈(Kate McGregor)、約翰·羅薩(John Roosa)、赫斯里·塞蒂阿萬(Hersri Setiawan)和瑪麗·祖布臣(Mary Zurbuchen)等歷史學家和活動家持續決心將印尼歷史的陰暗面暴露在陽光下,這給了我安慰,這可能不僅僅是虔誠的希望(Adam 2006; Budiawan 2004; Farid 2006; Jusuf et al. 2007; McGregor 2007; Roosa et al. 2004; Roosa 2006; Setiawan 2006; Zurbuchen 2005)。
結論:為未來能做些什麼?
還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減少未來反華暴力的可能性?經常有人認為根本原因是原住民和印尼華人之間感知的經濟差距。人們通常而籠統地說華裔控制著印尼經濟的70%(或更多)。這顯然是誇大,尤其是因為經濟的很大一部分屬於大型國有部門,並非處於華人控制之下。一個不那麼極端的表述是他們「控制70%的私人、企業、國內資本(而非更廣泛的經濟)」(Backman 2001, pp. 88–89)。另一方面,在1999年坎培拉的一次會議上,印尼大使維里約諾(Wiryono)引用了歸因於詹姆斯·利雅迪(James Riady)的數字,即印尼華人僅控制約10%的國民財富(Lloyd and Godley 2001, pp. 243)。無論這個較低估計的現實情況如何,公眾認知通常偏向較高的數字。
能對此做些什麼嗎?我不贊成為原住民印尼人採取平權行動的概念,部分原因是基於原則,因為這會讓最近消除對印尼華人歧視的運動倒退。這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它一方面將所有華裔同等對待(無論富有、中等收入還是貧窮),另一方面將所有原住民印尼人同等對待(無論富有、中等收入還是貧窮)。在我看來,純粹基於種族身份而不考慮他們是富有受過教育還是貧窮幾乎文盲,為超過97.5%的人口立法實行平權行動,這其中有某種內在的荒謬性。提議貧富差距可以且應該通過稅收制度如資本利得稅和累進所得稅來緩解,這可能看起來是烏托邦式的,但這在有良好法治的民主社會中相當常見。民主和法治在印尼語境中也可能看起來是烏托邦式的,但自1998年蘇哈托垮台以來,兩者都取得了一些進展。建立良好治理並通過政府和司法改革消除腐敗,將使一個社會公正的稅收制度成為可能;一個不基於種族而是基於需要和貢獻能力來區別對待的制度。
如果印尼人能夠成功做出這個誠然困難的轉變,背景將發生如此程度的變化,在同樣意義上,不再可能相信在印尼土地上公開舉行舞獅是挑撥性的,「反華暴力」將字面上變得不可想像。
參考文獻
Adam, Asvi Warman. Soeharto: Sisi Gelap Sejarah Indonesia. Yogyakarta: Ombak, 2004.
Ang, Ien. "Indonesia on My Mind: Diaspora, Internet and the Struggle for Hybridity". I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pp. 52–54. London: Routledge, 2002.
Backman, Michael. "The New Order Conglomerate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Indonesians, edited by Michael R. Godley and Grayson J. Lloyd, pp. 83–99. Adelaide: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 2001.
Budiawan. Mematahkan Pewarisan Ingatan: Wacana Anti-komunis dan Politik Rekonsiliasi Pasca-Soeharto. Jakarta: Lembaga Studi dan Advokasi Masyarakat (ELSAM), 2004.
Chin, Ung-Ho. The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2000.
Chirot, Daniel and Anthony Reid, eds. Essential Outsiders: Chinese and Jew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Europ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Coppel, Charles A. Indonesian Chinese in Conflict.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h ASAA, 1983.
———. "Chinese Indonesians in Crisis: 1960s and 1990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Indonesians, edited by Michael R. Godley and Grayson J. Lloyd, pp. 20–40. Adelaide: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 2001.
———. "Some Thoughts on the Size of the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in Indonesia". Indonesian-studies Yahoogroup (13 August) [accessed 2 July 2007].
———, ed.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in Jakarta, February 1996: The View from the Internet". In 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pp. 213–26.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2002.
Cribb, Robert, ed.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1966: Studies from Java and Bali. Clayton, Vic.: Centr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1990.
Editorial. "Riot-prone Nation". Jakarta Post, 12 May 2006.
Farid, Hilmar. "Political Economy of Violence and Victims in Indonesia". In Violent Conflicts in Indonesia: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Resolution, edited by Charles A. Coppel, pp. 269–8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Firdaus, Irwan. "Police Clash with Mob in Jakarta". Associated Press report, 13 May 2000 Yahoo奇摩 (accessed 17 July 2007).
Go, Robert. "Riot Raises Doubts About Law and Order: Officials Stress the Jakarta Unrest Was Not Linked to the Violence against the Chinese in 1998, But Followed a Raid on Illegal Video-compact-disc Sellers". Straits Times, 17 May 2000 (accessed from LexisNexis Academic).
Hajramurni, Andi. "Makassar Calmer After Student Protests". Jakarta Post, 12 May 2006a.
———. "Makassar Violence Highlights Ethnic Tension in City". Jakarta Post, 15 May 2006b.
Heidhues, Mary Somers. "Indonesia".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edited by Lynn Pan, pp. 151–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Heryanto, Ariel. "Rape, Race and Reporting". In Reformasi: Crisis and Change in Indonesia, edited by Arief Budiman, Barbara Hatley, and Damien Kingsbury, pp. 299–334. Clayton: Monash Asia Institute, 1999.
———. "Asal usul Mei 1998". Kompas, 13 May 2007.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mpunity versus Accountability for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Jakarta/Brussels: ICG Asia Report no. 12, 2 February 2001.
Jakarta Post. "More Chinese Tourists Expected to Visit Indonesia This Year". Jakarta Post, 2007a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detailbusiness.asp?fileid=20070628.M05&irec=4 (28 June 2007) (accessed 29 June 2007).
———. "China, RI Look Into Joint Maritime Ops". Jakarta Post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yesterdaydetail.asp?fileid=20070720.H07 (20 July 2007b) (accessed 13 August 2007).
———. "'Barongsai' festival to be held in Sragen". Jakarta Post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Archives/ArchivesDet2.asp?FileID=20070716.H05 (16 July 2007c) (accessed 13 August 2007).
Jusuf, Ester Indahyani, Hotma Timbul, Olisias Gultom, and Sondang Frishka. Kerusuhan Mei 1998: Fakta, Data & Analisa (Mengungkap Kerusuhan Mei 1998 sebagai kejahatan terhadap kemanusiaan). [Jakarta]: Solidaritas Nusa Bangsa (SNB) & Asosiasi Penasehat Hukum dan Hak Asasi Manusia Indonesia (APHI), 2007.
Kieval, Hillel J. "Middleman Minorities and Blood: Is there a Natural Economy of the Ritual Murder Accusation in Europe?" In Essential Outsiders: Chinese and Jew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Europe, edited by Daniel Chirot and Anthony Reid, pp. 208–33.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Kusno, Abidin. "Remembering/Forgetting the May Riots: Architecture,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Cultures' in Post-1998 Jakarta". Public Culture 15, no. 1 (2003): 149–77.
Leksono, Karlina. "The May 1998 Tragedy". I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Indonesians, edited by Michael R. Godley and Grayson J. Lloyd, pp. 55–60. Adelaide: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 2001.
Lloyd, Grayson J. and Michael R. Godley, ed. "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 I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Indonesians, pp. 232–51. Adelaide: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 2001.
Lochore, Laura. "Virtual Rape: Vivian's Story". In Intersections: Gender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Asian Context, 3 January 2000 <wwwsshe.murdoch.edu.au/intersections/issue3/laura3.html/>.
Mackie, Jamie, ed. "Anti-Chinese Outbreaks in Indonesia, 1959–68". In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pp. 77–138. Melbourne: Thomas Nelson, 1976.
McGregor, Katharine E. History in Uniform: Military Ide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onesia's Past. Singapore: ASAA in association with NUS Press, 2007.
Pizzey, Jack. Slow Boat from Surabaya: Through South-east Asia with Jack Pizzey. Videorecording: written and narrated by Jack Pizzey, Episode 2, "Rich, Clever, Homeless". Phillip Emanuel Productions, 1988.
Purdey, Jemma. "Problematizing the Place of Victims in Reformasi Indonesia: A Contested Truth about the May 1998 Violence". Asian Survey 42 (4 July–August 2002): 605–22.
———. "Anti-Chinese Violence and Transitions in Indonesia: June 1998–October 1999". In Chinese Indonesians: Remembering, Distorting, Forgetting, edited by Tim Lindsey and Helen Pausacker, pp. 14–40.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96–1999. Singapore: ASAA in association with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6a.
———. "The 'Other' May Riots: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Solo, May 1998". In Violent Conflicts in Indonesia: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Resolution, edited by Charles A. Coppel, pp. 72–89.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b.
Roosa, John, Ayu Ratih, and Hilmar Farid, eds. Tahun Yang Tidak Pernah Berakhir: Memahami Pengalaman Korban 1965: Esei-esei sejarah lisan. Jakarta: Lembaga Studi dan Advokasi Masyarakat (ELSAM), 2004.
Roosa, John. Pretext for Mass Murder: The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and Suharto's Coup d'état in Indonesia.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Sai, Siew Min. "'Eventing' the May 1998 Affair: Probl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Violenc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In Violent Conflicts in Indonesia: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Resolution, edited by Charles A. Coppel, pp. 39–5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Setiawan, Hersri. Kidung Para Korban: Dari Tutur Sepuluh Narasumber Eks-tapol. Pakorba, Yogyakarta: Pustaka Pelajar, 2006.
Sidel, John T. "Riots, Church Burnings, Conspiracies: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Indonesian Crowd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Violence in Indonesia, edited by Ingrid Wessel and Georgia Wimhöfer, pp. 47–63. Hamburg: Abera, 2001.
———. Riots, Pogroms, Jihad: Religious Violence in Indone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7.
Siegel, James T. "Early Thoughts on the Violence of May 13 and 14, 1998 in Jakarta". Indonesia 66 (October 1998): 75–108.
———. "Thoughts on the Violence of May 13 aand 14, 1998 in Jakarta". In Violence and the State in Suharto's Indonesia, edited by B.R.O'G. Anderson, pp. 90–125.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01.
Taufiqurrahman, M. "China, RI Tighten Cultural Connection". Jakarta Post, 28 June 2007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yesterdaydetail.asp?fileid=20070628.H08 (accessed 29 June 2007).
Tan, Mély G. "The Indonesian Commission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Violent Conflicts in Indonesia: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Resolution, edited by Charles A. Coppel, pp. 229–41.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Tay, Elaine. "Global Chinese Fraternity and the Indonesian Riots of May 1998: The Online Gathering of Dispersed Chinese". Intersections: Gender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Asian Context, 4 September 2000 <wwwsshe.murdoch.edu.au/intersections/issue4/tay.html>.
———. "Discursive Violence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May 1998 Riots". In Violent Conflicts in Indonesia: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Resolution, edited by Charles A. Coppel, pp. 58–71.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TGPF [Tim Gabungan Pencari Fakta]. "Final Report of the Joint Fact-Finding Team (TGPF) on the 13–15 May 1998 Riot, Executive Summary, 23 October 1998". I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Indonesians, edited by Michael R. Godley and Grayson J. Lloyd, pp. 332–60 (Appendex 2). Adelaide: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 2001.
The, Siauw Giap.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A Review Article". Kabar Seberang, 7 July 1980, pp. 114–30.
Wang Gungwu. "Islam Versus Asia's Chinese Diaspora". Project Syndicate, July 2002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ungwu1 (accessed 27 June 2007).
Wibowo, Ignatius. "Exit, Voice and Loyalty: Indonesian Chinese after the Fall of Soeharto". Sojourn, vol. 16, no. 1 (2001): 25–46.
Wikipedia. "Chinese Indonesian". Chinese Indonesians - Wikipedia (accessed 17 July 2007).
Zurbuchen, Mary S. "History, Memory and the '1965 Incident' in Indonesia". Asian Survey 42, no. 4 (2002): 564–82.
———, ed. Beginning to Remember: The Past in the Indonesian Present.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機研] 委內瑞拉共產黨與馬杜羅的關係](/content/images/size/w600/2026/01/2020-10-25-PCV-Partido-Comunista-de-Venezuela-rgb.png)